耿寶昌:故宮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個家

-
小陶陶
2019-04-26 《深圳商報》2019
13220
要說當(dāng)今中國古陶瓷鑒定界坐頭把交椅者,那無疑當(dāng)屬92歲的故宮文物鑒定專家耿寶昌先生了。老爺子從事瓷器鑒定70多年,一生閱寶無數(shù)。人送外號:“瓷圣”、“人間國寶”。對此他總是淡然一笑,一如既往地低調(diào)謙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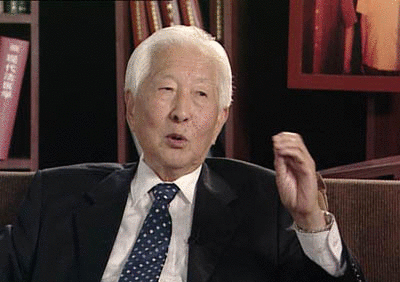
在近日英國東方陶瓷學(xué)會授予“希爾金獎”儀式上,記者在故宮見到了耿老。老爺子耳不聾,眼不花,腰板筆直,滿頭銀絲,根根透亮。采訪時記者的問題剛一提出,他就開腔作答,語速挺快,時不時還嘣出些新詞。
從小學(xué)徒到大掌柜
耿寶昌1922年出生于北京,耿家世代經(jīng)營珠寶翠玉,祖父曾是北京頗有名氣的翠玉專家,遺憾的是,到了父輩,家境日漸沒落。14歲時,高小畢業(yè)的耿寶昌便到京城著名的“敦華齋”里做伙計,這家古玩店的主人就是人稱“宣德大王”的孫瀛洲。
記者:“敦華齋”當(dāng)時是京城極負(fù)盛名的文物店,據(jù)說它每年僅官窯精品庫存就有上萬件?
耿寶昌:長期是一萬多件存在,反正現(xiàn)在比一個大博物館不少。最初我跟師傅做學(xué)徒,干的都是體力活。敦華齋每年都要來十幾個學(xué)徒,但能留下的也只有幾個人。后來師傅看我踏實勤奮,就讓我管理庫房。
每年到年底沒啥事情了,大家都休息了,咱經(jīng)管這事情,就必須從頭做起,左一遍右一遍至少是要查看三遍,費時間很長。這對我來說當(dāng)然是個好事,通過給文物貼號、換號,熟悉文物。借清洗、擦拭、搬動文物,體驗各類文物的手感。師傅讓拿什么東西看,一說我就知道是什么,在哪個位置。
看著那么多官窯精品,就好似上了一次古瓷鑒定領(lǐng)域的“哈佛大學(xué)”。
記者:做學(xué)徒講究勤快、好學(xué),您是不是經(jīng)常抓住機(jī)會向老師求教?
耿寶昌:那時候沒有講課,不像現(xiàn)在這個那個學(xué)習(xí)班的。老師不給講義,全在于自己聽,老先生們講什么你就往腦子里面裝。他們說這個生意怎么樣,哪兒發(fā)現(xiàn)一個什么東西,那東西怎么一回事,你就聽。
記者:聽說有一次您聽得太入神了,給客人點煙時竟燒了自己的手指?
耿寶昌:就是手指頭這兒缺一塊。你聽我說,是兩個老先生坐著對面,這擺著茶碗,我就在旁邊穿著長袍規(guī)規(guī)矩矩站著。老先生都是抽旱煙,旱煙呢他自己裝,裝好了我這手上拿著一盒火柴,在旁邊這么一點,“噌”給人點著了。點完了繼續(xù)聽,沒想到這火柴盒也呼呼呼地著了,著了也不敢扔啊,你扔了你知道燒著誰啊,所以就忍著。這就讓它呼呼去吧,手指頭就著了點,結(jié)果這兒就起了一塊皮那么厚,等它干掉以后,就掉了。
記者:那您什么時候出師的呢?
耿寶昌:當(dāng)了10年的學(xué)徒后,1945年,我在今天琉璃廠那地方開了自己的文物店——振華齋。那時候我24歲,我就牢記師傅的教誨,“做瓷器鑒定絕不能把眼睛看窮了”,我只看最精美、最珍貴的。
“火眼金睛”是如何煉成的
記者:聽說您現(xiàn)在兩眼的視力還都是1.5?
耿寶昌:我86歲的時候視力還都是1.5,到了醫(yī)院大夫都很吃驚,說老爺子你怎么搞的。我說我沒什么奇怪,我跟著大家一樣。就老伴一走了以后,我一個眼的視力下降到1.2了。
記者:您的“火眼金睛”是怎么鍛煉出來的?
耿寶昌:談不上“火眼金睛”。當(dāng)年跟孫瀛洲先生學(xué)習(xí)時,孫老的藏品量大而精,而且面廣,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就具備了良好的學(xué)習(xí)環(huán)境和條件,在這一領(lǐng)域就如同進(jìn)了高等學(xué)府的科研室,因此才有成為專業(yè)人員的可能與條件。再加上我對自己要求很嚴(yán)格,不斷鞭策自己,力求勝任工作。
記者:孫瀛洲先生對您要求是不是特別嚴(yán)格?從師父那里您學(xué)到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?
耿寶昌:感受最深的是老師對學(xué)生要求很高、很嚴(yán)格,而且常常對學(xué)生進(jìn)行考試。當(dāng)時我曾立志要在幾年內(nèi)學(xué)到一些鑒定方面的功夫,所以就特別認(rèn)真、刻苦地學(xué)。當(dāng)時我想,至少也應(yīng)學(xué)到老師所說的“三不”,就是“經(jīng)得起三問問不倒、再問面不更色、經(jīng)得住三斧砍不倒”。我從師父那里學(xué)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嚴(yán)謹(jǐn)刻苦的治學(xué)精神。
記者:現(xiàn)在您自己培養(yǎng)的徒弟很多已是文博界的棟梁,您選徒弟的標(biāo)準(zhǔn)是什么?您是怎樣培養(yǎng)他們的?
耿寶昌:我對來學(xué)習(xí)的同志都以誠相待,基本是延續(xù)了從孫瀛洲老師那里學(xué)來的方法來教育學(xué)生,高標(biāo)準(zhǔn)、嚴(yán)要求。對學(xué)生提的問題,精心細(xì)講,耐心詳說。
我和故宮是“魚”與“水”的關(guān)系
新中國成立后,故宮的文物拯救工作日益展開,1956年,受聘到故宮工作的孫瀛州,向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吳仲超舉薦了自己的得意門生——34歲的耿寶昌。于是,耿寶昌成為故宮古器物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。
故宮博物院東南角的南三所,曾經(jīng)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讀書的地方,后來故宮古器物部的辦公室就設(shè)在這里。從進(jìn)入故宮那天起,耿寶昌在這里工作了半個多世紀(jì)。1986年,他將自己珍藏的瓷器、銅器等文物80多件捐獻(xiàn)故宮博物院。
記者:還記得您1936年第一次參觀故宮時的情景嗎?
耿寶昌:那是在“七七事變”之前,當(dāng)時正是春天,故宮里非常殘破,到處是雜草和垃圾。門票是一塊大洋。我記得在鐘表館看到過一個可以在一塊板子上滾動的鐘表。20年后我來到故宮工作,那個東西還在那里。
記者:到故宮工作之后有沒有讓您覺得非常開眼的地方?
耿寶昌:那太多了。比方說故宮里邊的宋代五大窯。外邊多你能看一個兩個,這里邊一看是十個八個,十個二十個。機(jī)會難得。琺瑯彩在外面見也是少數(shù)的,到故宮里面一見好多好多。很多東西能看得面面俱到,你以前知道一個,現(xiàn)在你知道十個。就跟扇面一樣,首先放眼自己單位,海內(nèi)、海外整個一了解,齊了,你全有了,這是軸心。
記者: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,故宮籌備了一次中國出土文物展覽。您曾經(jīng)只身一人護(hù)送500件國寶出國展出,能講講那次“文物外交”的經(jīng)過嗎?
耿寶昌:1973年,經(jīng)過兩年緊張籌備的中國出土文物展即將開幕。按照計劃,我押載500多件珍貴文物,飛往展覽的第一站法國巴黎。飛機(jī)上的參展文物件件價值連城,我一路上忐忑不安,腦袋里一直回響著臨行前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話:“人在物在。”幾個小時后,飛機(jī)在阿聯(lián)酋的迪拜機(jī)場中轉(zhuǎn)加油時,我遭遇了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驚心動魄——阿聯(lián)酋機(jī)場發(fā)生了世界上第一起劫機(jī)事件。
到了那已經(jīng)是夜晚了,我當(dāng)時第一次出國,也覺得特別新鮮,我一看這怎么回事啊,機(jī)場周圍全是是警察、軍隊,都拿著槍圍著這飛機(jī)。這個飛機(jī)是英國來的專機(jī),什么都沒有,就裝著一部分東西跟我,還有英國使館一個文化參贊隨機(jī)回去。他說等下咱們下飛機(jī),我說不去不去,出來的時候有交代,萬一出了事怎么辦呢,是吧。
在機(jī)艙內(nèi)等了一個小時,飛機(jī)終于又起飛了,一場虛驚之后,我們安全抵達(dá)了巴黎戴高樂機(jī)場。
記者:這次展出的效果怎么樣?
耿寶昌:這次展出歷時四個月,參觀人數(shù)高達(dá)36萬人次,帶給巴黎人的震撼不言而喻。
在法國楓丹白露博物館,我也受到了強(qiáng)烈的刺激。我一看這博物館里全是我們中國的東西,后來我到日本也去過,一看全是中國東西。那真是,比我們國內(nèi)東西多得多了,全是給人拿走的。那就是一種身上出汗,覺得這怎么搞的呢?那種感情。尤其他們寫得清清楚楚,這個東西是哪個地方,哪個省哪個市哪個縣哪個村的出土的,感觸很大。
記者:明年故宮博物院將迎來建院90周年紀(jì)念日,您會參與慶典活動吧?
耿寶昌:在慶祝故宮博物院80華誕時,我曾參與“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展”的籌備工作,親自到庫房挑選展品。明年90周年院慶期間,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將隆重推出“清淡含蓄——故宮博物院汝窯瓷器展”,并召開專題汝窯學(xué)術(shù)研討會,現(xiàn)在正在積極籌備,我仍然會為此項工作盡自己的一份力,包括與同事一道為展覽挑選展品。
記者:您對“90歲”的故宮博物院有什么期許?
耿寶昌:作為一名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了半個多世紀(jì)的老職工,親眼目睹了它近60年來所經(jīng)歷的風(fēng)風(fēng)雨雨和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業(yè)績,因此,就更加期待建院90周年紀(jì)念日的到來。
我對故宮博物院的感情可以說是“魚”與“水”的關(guān)系,故宮博物院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個家。我的職責(zé)是研究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歷代陶瓷藝術(shù)品,守護(hù)好這些文化遺產(chǎn),為弘揚(yáng)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出自己的一份力。
收藏應(yīng)是種文化享受
幾十年當(dāng)中,耿寶昌為國家鑒定了數(shù)萬件一級文物。在他的鑒定生涯中最為人稱道的一次,就是1994年他從香港的拍賣會上以110萬元拍賣回的成化罐。
歷史上明代成化憲宗皇帝非常喜歡小器物,那個年代最常見的官窯瓷器都是碗、盤等小件,故有“成化無大器”之說。而這個通高31厘米,口徑17厘米的成化罐則是現(xiàn)存少有的大件器物。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四只,而故宮的這個是唯一一個帶蓋的最完整的成化罐。雖然有人認(rèn)為這個帶蓋的成化罐是假的,這個爭論一直持續(xù)到了今天。但是現(xiàn)在它的身價已經(jīng)漲至2000萬元。
記者:現(xiàn)在熱愛瓷器收藏的人越來越多,您怎么看待這個現(xiàn)象?
耿寶昌:過去瓷器在中國人心目中并沒有太高的地位。以前故宮對外展示館藏瓷器時,觀眾一看,又是破瓷器,連(展廳)門檻都不進(jìn)。隨著現(xiàn)在中國古瓷器價格的迅速升值,觀眾對于故宮館藏瓷器的熱情也越來越高。現(xiàn)在一有館藏珍品瓷器展,展廳內(nèi)的人多得擠不動。
故宮100多萬件藏品,瓷器和書畫就各占三分之一。舊社會青銅器價格高,后來書畫價格高,現(xiàn)在瓷器的價格漲了上來。但是與書畫相比,瓷器的價格仍有上升的空間。
記者:故宮珍藏的瓷器,您是不是都過過眼?
耿寶昌:這50多年來連看帶動手,很多都有印象。那時候沒有電腦,比如說到某件瓷器,你必須知道在哪里。故宮藏品中36萬件瓷器,我只能說有些認(rèn)識吧。
我現(xiàn)在每天上午仍然堅持要去故宮轉(zhuǎn)一轉(zhuǎn)。我這“90后”也還要不斷學(xué)習(xí),要溫故而知新,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博大精深。做這一行需要知識,更需要實踐。
今天的人會更多地從經(jīng)濟(jì)角度看待一件文物,但我覺得收藏應(yīng)該是一種真正的文化享受,不論金錢和價值,只看藝術(shù)和歷史。
記者:您的《明清瓷器鑒定》是最權(quán)威的瓷器收藏鑒定指導(dǎo)書了,您還有修改再版的計劃或者出其它著作的打算嗎?
耿寶昌:我的《明清瓷器鑒定》一書原本為培養(yǎng)專業(yè)人員快速掌握明清瓷器鑒定方法而作,因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陶瓷器以明清時期的最為多見,因此,若能先從明清瓷器入手學(xué)習(xí)古陶瓷鑒定,就可以使更多的人掌握明清瓷器鑒定方法,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這本書早已售罄,目前正在進(jìn)行修訂,準(zhǔn)備再版。

記者:瓷器中您最喜歡哪一種?
耿寶昌:我最喜歡的是宋代的素色瓷。那是一種文人的審美情趣,比如天青色的鈞窯,非常地雅致。
記者:瓷器也是當(dāng)前文物造假的重災(zāi)區(qū)之一,您怎么看待這種亂象?您能給大家一些提醒嗎?
耿寶昌:這從宋代就開始了,不管是什么青銅器,書畫,瓷器,都仿前朝的,早就有了。
記者:收藏家多長壽者,您92歲身體還這么好,能否給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您的養(yǎng)生之道?
耿寶昌:我今年已92歲,還能堅持上班,很多人都以為我有什么特殊的養(yǎng)生之道,其實,我就是一個平凡的工作者。我想,每個人只要能做到任勞任怨地工作、心地平靜、生活規(guī)律、知足常樂、沒有貪心、與人為善、愛惜生命、愛活動、胃口好,就一定能長壽。
責(zé)任編輯:admin
















